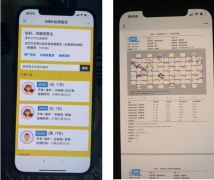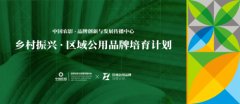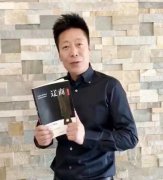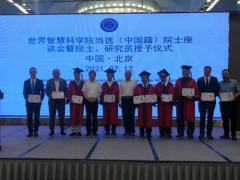酒精滥用的危害与预防

文/胡月
酒是一种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产生依赖性的特性,个体长期的不当饮酒容易产生酒精滥用行为。同时,酒精滥用也是导致200多种疾病、伤害和其他健康状况的原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酒精滥用是全球构成健康威胁的第三大风险因素,每年因此造成的死亡人数逾300万。
酒精滥用会严重影响身心健康,与此有关的精神疾病包括重度抑郁、持续性抑郁症、人格紊乱、燥郁症、轻度燥郁症、恐慌症、恐惧症、广泛性焦虑症、人格障碍、思觉失调、自杀和神经认知功能的损害(例如工作记忆、情绪、认知控制、视觉空间能力等)。
慢性酒精伤害容易引发大脑前额叶皮层DNA氧化性损伤,该脑区负责认知功能,例如工作记忆、冲动控制、决策执行等。酒精滥用者的社交技能会显著受损,因酒精滥用而受损的社交技能包括感知面部情绪、情感调节、心智功能等。由于青春期是大脑发育的敏感期,青少年的有害酒精使用最容易造成神经认知功能,尤其是执行功能和记忆功能的紊乱与受损。

酒精使用障碍是由遗传、社会心理和多种环境因素导致的。遗传对酒精使用障碍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酒精使用障碍的遗传率约为60%;然而,与其他慢性健康状况一样,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也受到个体遗传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父母的饮酒模式也可能增加孩子形成酒精使用障碍的可能性。此外,个体患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受其首次饮酒时间的影响。当首次饮酒行为发生在青少年时期,个体在成年后期更容易患有酗酒使用障碍。在26岁及以上的人群中,15岁之前开始饮酒的人患有酒精使用障碍的可能性是21岁或更晚才开始饮酒的人群的5倍多,这一群体中女性的风险高于男性。并且,个体的精神健康状况和创伤史也与酒精使用障碍有关。广泛的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与酒精使用障碍共病,并与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增加相关,有儿童创伤史的人也易患酒精使用障碍。
鉴于青春期这个阶段所特有的特殊风险和易塑性,在预防干预工作中需要更多的重视青少年的酒精滥用行为。对于青少年酒精使用障碍的治疗和干预,可重点关注青少年个体不良童年经验对其的影响(如校园霸凌),这是青少年早期酒精滥用的重要风险因素。包括青少年校园应急事件管理、家庭访谈和合理情绪管理等方法已被证明是预防和治疗青少年冲动性酒精使用障碍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对青少年积极开展酗酒危害教育,并帮助他们关注自己的饮酒行为,可有效改变其对饮酒的看法,帮助他们避免酒精滥用和相关酗酒危险行为的发生。
另外,针对已经患有酗酒行为的个体,其可以先尝试适当减少饮酒数量,保持在“适度饮酒”的范围,从而降低绝对饮酒数量;此外,酗酒患者可通过社会支持互动等方式共同协助达到戒酒的目的;一些针对性的认知行为疗法,例如训练个体关注觉察自己当下的感受和情绪体验,保持情绪控制的稳定,可有效减少饮酒冲动。
最后,在社会层面,为酒精使用障碍的个体创造一个积极肯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可有效帮助其治疗。具有酗酒行为的患者寻求治疗的一个重要障碍是与酒精滥用相关的社会性污名化。当社会文化氛围将酗酒行为与脆弱、不负责任等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酒精使用障碍的个体不敢公开病情,最终病情难以得到有效管理和治疗。酗酒行为的污名化与抑郁程度的增加有关,会导致焦虑程度增加、自尊水准降低、睡眠品质变差等。有效的社会支持可为酒精滥用患者降低污名化带来的不利影像,并帮助那些在酒精滥用中挣扎的个体克服相关的负面情绪,从而积极地去寻求所需治疗。

贾天野,现任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青年研究员(博导),获得2021年国家自然基金委优秀青年项目及2018年上海市浦江学者项目的支持。曾就职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心理学及神经科学研究院(在心理学及精神疾病领域排名全球第二)。长期从事人类行为及精神障碍的神经生物学机理研究,特别是基于大样本影像遗传学数据对人类行为及精神障碍的神经生物学机理进行探索。已发表SCI论文4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身份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PNAS,Science Advances,Molecular Psychiatry及JAACAP等相关领域的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